
- 本社经常接到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澳门、新加坡及本港等国家、地区的一些老年作者寄来的纸质书稿,有些书稿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给我们的审稿工作带来不便,故友情提醒:本社从现在起不再接受纸质书稿,一律改为电子书稿,书稿统一发邮箱zggjwycbs@163.com,请大家周知。
- 紧急通知
本网站多次受到黑客攻击,不少图书资料丢失,若您的图书资料在本网站无法查到,请发邮件至zggjwycbs@163.com与本网站取得联系,特此通知。
唯光论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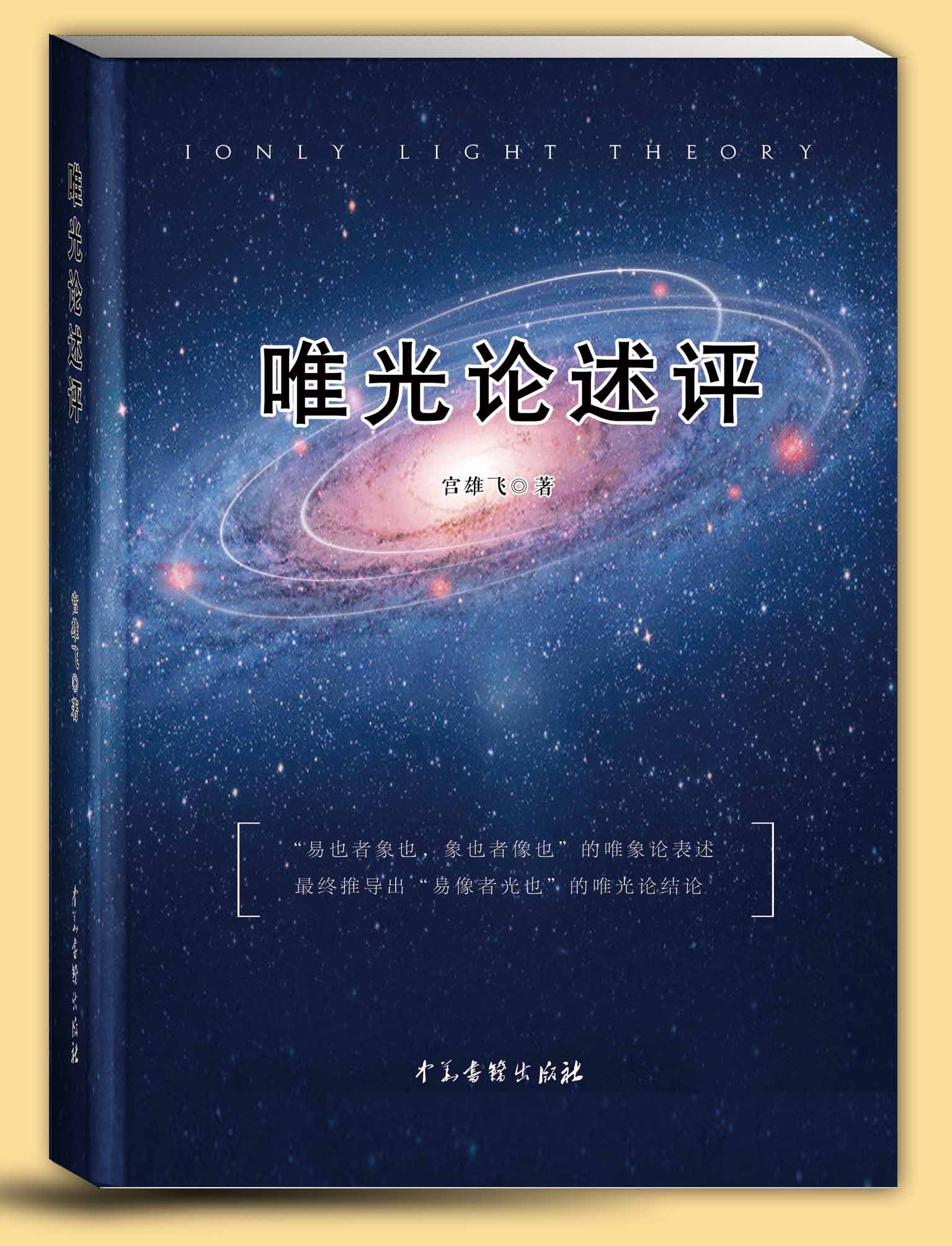
序言:光的生命礼赞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旧约》创世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此,我们与光结伴而行,正像一个人与他形影不离的影子一样。如果有谁忘记了她,他的影子会提醒他。如果他说,他在睡眠中淡忘了,他头顶上的星光——你可以想象那是她明慧狡黠的目光,在星空默默地注视着他——那位被誉为哲学界的哥白尼、一生只崇尚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人懂得,那冥冥星空中的默默注视,意味着什么。
光为何方神圣?“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徼,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两千五百年前,东方一名为老聃的智者,面对洪荒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之光耀,对她进行了细致的正面观察: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综合为一,一乃无形。后来有人佐证: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无像之形,莫贵于光。光乃无状之状,无象之象,上徼下昧,上显下隐,但显而不明,隐而不昧,不见首尾,唯现其“中”,守中而敛,绵长无尽,似无而实有——老聃灵机一动,从光开始了他的“无中生有”的睿智之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当这位被后人尊奉为“老子”的圣贤哲人说“道出现在 x 处”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原因”是什么,它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这种命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位耄耋老者振振有词地说:恒常,我无心观察道的细微奥妙,但有意观赏其光耀的一面。“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此”即“光”也,我所以凭“光”认识万物起源的情状也。光被视为道之子,功德无量,万物归焉,却又“道中而用”,无为而治,“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故老聃说,(我)常无欲也,可名於小。常有欲也,可名为大。大矣哉!大矣哉! “吾不知谁子?象帝之先。”
在西方,公元前五百年,古希腊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试图把光与火结合起来。他认为,世界的始基就是火,“一切转为火,火又转为一切”。我们完全可以形象地理解这个理论:一盏油灯的火焰看起来好像一个不动的东西,但是油一直在被吸上来,燃料变为火焰、发光,油烟同时在燃烧中落下来,因此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类此的转换过程。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燃烧 - 熄灭”周而复始的过程。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燃烧中发出光来,这个燃烧发光的过程就是“逻各斯”。有趣的是,这个“逻各斯”中文译为“道”,逻各斯实际是一个与“道”相同的概念,作为事物的规律潜在,而她们的“显在”就是“光”。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是: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在于认识“逻各斯”。
奴斯”或心智说是一个与“逻各斯”相近的概念。它是由古希腊另一位哲人阿那克萨哥拉首先提出来的。希腊文“Nous”有心智、理智、智力、机智、理性、精神、常识等译法,“在一切事物之中有一切事物的一部分,但心智除外,而且在某些事物之中也有心智存在”——罗素的意思是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但不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一切事物的一部分”。后来,这个概念由普罗提诺发挥到极致。普罗提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所谓“太一”或“元一”,太一有时候被称之为“神”,实际上这是一个将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结合起来的概念,我们还记得,在犹太教那里,神说要有光才有光;而在这里,“太一”是神和光的结合,神人合一,这是西方的“天人合一”的变种;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是中国独特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阐释。所以,“太一”这个概念,是比较接近于老子的“道”的涵义的。只不过“神说要有光”在这里变成了“神就是光”。所以,“nous”被普罗提诺认为是“太一”看见自身时所依恃的“光明”。这样,当我们“被神明所充满、所鼓舞”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见到了 nous,而且也见到了太一。 “在与神明相接触的那一瞬间,是没有任何力量来做任何肯定的;那时候没有工夫这样做;根据所见来进行推理,乃是以后的事。我们只知道当灵魂突然之间被照亮了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了这种所见。这种光亮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来的,这种光亮就是至高无上者;当他像另一个神那样受到某一个人的呼吁而带着光亮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在面前;光亮就是他来临的证据。这样,没有被照亮的灵魂就始终没有那种所见;但是一旦被照亮之后,灵魂便具有了它所追求的东西。而这就是摆在灵魂之前的真正的目的:把握住那种光明,以至高无上者——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原则的光明来窥见至高无上者,——窥见那个其自身同时也就是获得这种所见的方法的至高无上者;因为照亮了灵魂的正是灵魂所要窥见的,正犹如惟有凭借着太阳自身的光明我们才能看到太阳一样。”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流溢”出来的,犹如太阳辐射出光——普罗提诺如斯说。在他的著作中,“善”与“光明”相提并论。请看普罗提诺是怎样赞美“神”也即“光”的——他们本身就在一切之中;因为一切都是透明的,没有什么是黑暗的,没有什么是能阻碍的;每一个生存对于任何另一个生存都是通明透亮的,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光明是通过光明而进行的。他们每一个的自身之中都包含着一切,并且同时又在另外的每一个之中都见到了一切,所以处处都有一切,一切是一切而每一个又是一切,这种光荣是无限的。他们每一个都是伟大的;微小的也是伟大的;太阳在“那里”是一切的星而每一座星又都是一切的星与太阳。每一种里面都以某种存在方式为主导,然而每一种又都彼此反照着一切。普罗提诺式的“龙场悟道”也是饶有趣味的,“于是我便窥见了一种神奇的美;这时候我便愈加确定与最崇高的境界合为一体;体现最崇高的生命,与神明合而为一;一旦达到了那种活动之后,我便安心于其中;理智之中凡是小于至高无上者的,无论是什么我都凌越于其上:然而随后出现了由理智活动下降到推理的时刻,经过了这一番在神明中的遨游之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此刻的下降是怎么回事,灵魂是怎样进入了我的身体之中的,——灵魂即使是在身体之内,也表明了它自身是高尚的东西。”光,即是他心目中的至高无上者。而 nous,只不过是光的“逻各斯的一种新的形式。
中世纪,在经院哲学的前身,教父哲学那里,“上帝”里面已经有一个与上帝同样先在的“逻各斯”或“道”,或称作上帝的“话”,随之上帝就用发“话语”的办法,借“逻各斯”或“道”进行“创世纪”。所以,这里面包含着物质与上帝同在的意思,上帝可以与“逻各斯”“道”同义而语,上帝甚至是“实在”的另一种不同的说法。上帝只是一种“拟人化”或“拟神化”或“偶像化”的“实体”。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创造“实体”这个概念时已经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上帝这种“实体”是经过希腊传统加上奥尔菲神秘主义演绎而来的。所以,“上帝与光同在”。这集中表现在奥古斯丁的著述中。他说上帝赐给他“一些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虽然字句有些出入,但根据不同的理由,我于其中读到以下的旨趣,“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他就没有万物:他所创造的是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而黑暗却不接受光。”虽然说人的灵魂“给光作见证”,但他本身“却不是光”,只有上帝、上帝的道,“才是真光,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并且“他在世界之中,而这世界也是借着他创造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
岁月蹉跎,十三世纪,邓斯·司各脱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否有任何确实而纯粹的真理,不被非经创造的光的特殊照耀而能自然地为一个过路者的理智所知晓?”
文艺复兴时期,康帕内拉把太阳崇拜为神,神就是一切,自然界只是神所流溢出来的,这种观点我们似曾相识。太阳创造自然界中的事物,但太阳并不是离开自然界而存在的。康帕内拉从一切生物离不开阳光而想到太阳的神圣性质,因而创立了这种以太阳为神的宗教。但在这方面,他不是始作俑者。米斯拉教起源于东方波斯,在公元三世纪的后半叶,它成了基督教的激烈竞争者,米斯拉是波斯的光神、太阳神,是一个主宰战争的神,而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是组成有史以来古波斯帝国信仰的主要部分。据说米斯拉的信徒在军队中非常之多,不仅在东方,西方也是这样。米斯拉之所以没能进驻天国,是因为基督把持天国的钥匙拒不发给他签证。但对于拥戴他的东方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件好事。米斯拉在现代的复活便是唯光论的诞生。
在中国,太阳神崇拜似乎是较之祖先崇拜为更普遍而重要的信仰之一。古文献所见,不仅有古帝为太阳神的传说,古帝因梦日或红光而降生的故事,而且无论是祀典、歌舞、服饰、建筑或文学等方面,都广泛地与太阳相关。如古代人君、天子,就是人间太阳神或其替身。大昊、少昊、炎帝、黄帝,从字义上就都是光帝,即太阳神。天官五帝则不过是四季不同方位的太阳神而已。故一年四季中,天子居于明堂,其意也不过是人间的太阳神。中国的主导性哲学概念“道”,起源于“天道”,道教也起源于上古崇拜太阳和北斗的天文学。
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巅峰时代,哥白尼和哈维在各自的领域里完成了对光的生命礼赞。首先是哈维,“心脏是生命之源,是小宇宙的太阳,这正如太阳接下来很可能被认定是世界的心脏那样。因为正是心脏的功效和搏动,才使得血液运动不息、完善无瑕、易于供给营养,并且防止了腐烂和凝结。正是这种普通的神性,在履行其职责时,滋养、抚育了整个身体,并加快了整个身体的成长。它的确是生命的基础、一切活动的源泉。”他对光的生命礼赞凝聚在他的杰作《心血运行论》中。
然后是创作了《天体运行论》的哥白尼——
“太阳位于万物的中心。的确,在这座最辉煌的天宇中,它能普照万物,同时又照亮自己。难道还有谁能把这盏明灯放到另一个或者更好的位置上呢?因此,它当之无愧地被一些人喻为宇宙之灯,被另一些人称为宇宙之心灵,还被一些人比作世界的主宰。
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称它为)看得见的上帝,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厄勒克特拉把它叫做万物洞察者。因此,毫无疑问,太阳位居王座统辖着周围的星族。如果说哈维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小宇宙”的人,哥白尼的对象则是作为“大宇宙”的天;两个人的结合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谐和。
西方具有深远影响的“化学论哲学”、所谓赫尔墨斯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在其模仿赫尔墨斯风格写的太阳颂词中说,“没有什么可像光一样充分地显示善(即上帝)的本质。首先,光是各种看得见的物体中最灿烂、最清晰者。其次,没有什么可以像光一样传播得如此容易、如此广阔、如此快捷。其三,它无害地穿透一切物质,轻柔得就像爱抚一般。其四,光带来的热养育并滋润着万物,是宇宙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同样,善被四处传播,抚慰着万物,吸引着万物。善不必强制实施,而是通过和善一起存在的爱来施与万物,就像(伴随着光的)热一样。这种爱吸引着万物,以使万物自由地接受善……也许光本身就是天国神灵的视觉,或者用于观察、用于遥控、用于将万物同天国联系起来,既不远离天国也不与外来物相混同……仰望天空,我为你们,神圣天国的公民祈祷……太阳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上帝,那么谁敢否定太阳呢。”
启蒙运动时期,“人类正当的研究对象是人”。但光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在近代、现代科学日益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高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认识到光在生命活动中的不可或缺,对光的顶礼膜拜终于上升到一个理性阶段:光究竟为何物?早在罗马时代,伟大的卢克莱修在其不朽著作《物性论》中提出,光是从光源直接到达人的眼睛的,但是他的观点却始终不为人们所接受。对光成像的正确认识直到公元一千年左右才被一个波斯的科学家阿尔哈桑所提出: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物体,只是由于光从物体上反射到我们眼睛的结果。基于光总是走直线的假定,欧几里得研究了光的反射问题。托勒密、哈桑和开普勒都对光的折射做了研究;荷兰物理学家斯涅耳则在他们的工作基础上于 1621年总结出了光的折射定律。最后,光的种种性质终于被费尔马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法则:光总是走最短的路线。这是符合马赫的经济思维原则的。光学作为一门物理学科被正式确立起来。自牛顿时代以来,光不再是弥漫四大、纯粹、无色的神秘物质,不再是上帝的住所,而成了一个物理现象,它的规律可用反光镜和透镜来研究,它的颜色可用三棱镜来分析。那种把天和地区别开来的传统看法,经过整个漫长的中世纪,终于被伽利略与牛顿把这种看法打破了。他们用数学方法与观察方法证明,通过实验确立的落体定律在整个太阳系中一样适用。可是要最后证明天地同一,不但需要天地在运动方面是类似的,而且还需要证明天地在结构上与组成成分上也是类似的,还需要证明构成地上物体的常见化学元素,在太阳、行星与恒星的物质中也一样的存在。这好像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却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解决办法是通过光谱分析来完成的。科学家从光
谱里得到多种化学元素,或者说光不断地产生化学元素,这些化学元素从前人们只是从他们赖以居住的地球上得到,现在却从天外来客的光中得到。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同时光与辐射热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也得到充分证明。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关于电子的发现终于解决了古希腊原子论者提出的问题:即不同的物质是否有共同的基础的问题。电子被认为是原子的一部分,无论它的性质如何,它所含的“物质”均为组成原子的共同成分。而这项伟大的新发现与不久前的一项研究,颇有关联之处。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把光与电磁波联系起来,爱丁顿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光与电磁波与万有引力相提并论。按照麦克斯韦的理论,光既然是一种电磁波系,那么光必定是由振荡的电体所发出的。由于光谱是元素所特有的而不是元素的化合物所特有的,所以这些振荡体必定为原子或原子的一部分。后来他的理论为洛仑兹和塞曼所证实。物质或以电子的形式、或以电磁波的形态与光相通。按照量子论,光在发射与吸收的刹那间,即不是弗雷内尔的稳定的“以太波”,也不是麦克斯韦与赫兹的连续电磁波。它更好像是一团一团的微量的能量所组成的流,这些细团的能量几乎可以看做是光的原子(光子),虽与牛顿的微粒不同类,但却与之相当。能量实际上是构成所有基本粒子、所有原子、从而也是万物的实体,并且能量也是运动的根源从而也是世界上一切变化的根源。已经发现的两个“普适常数”都与光有关,人们翘首以待第三个普适常数尽快地“认祖归宗”,到那时,鼎足而立的物理大厦将巍然耸立在宇宙之林!
难怪牛顿在其皇皇巨著《光学》一书中质疑说:“庞大物体和光不是可以互相变化的吗?物变为光与光变为物,是同似乎乐于变化的自然程序十分符合的。恒星可能正在化为辐射,宇宙间物质的命运不是直接化为空间的辐射,就是变成具惰性而不活动的东西,如构成我们世界的主要物质。”
在我们的主角还没有粉墨登场之前,让我们复述一下光的波动说得有趣现象——是什么原因迫使快乐的几率波“坍缩”而显形为粒子的呢?量子力学目前标准的答案:是因为“有人”观察了。这是一个非常新奇惊人、非常有争议的答案。讲的直接点,我们可以说,一个光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人”观察了。微观世界里物质的波粒二象性似是而非的“存在”状态,以及“有人”的观察对这种“存在”的干涉作用,是量子力学揭示出来的非常深层次的几乎不可理喻的物理现实。虽然量子力学在物理各个领域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基本理论上怎样去解释那些不可理喻的物理现实,仍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从中所受到的启发是:哲学不能没有直觉的作用。早在十九世纪,杰文斯就在他的《科学原理》一书中断言,在科学的发现方法中,直觉具有崇高的地位。怀德海也持这种观点:为了重新考虑科学假说的基础,就必须回到对真实事物性质的更具体的观点上去,必须把它的基本概念看成是从这种直觉中得出的抽象概念。世界上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对太阳的崇拜、对光的仰慕都是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光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朋友,又是送别我们的最后一个朋友。像光贯穿我们的生命史一样,它也贯穿着整个人类的智慧史。从冥冥中宇宙的第一次大爆炸,到遥遥无期的暗能量流,光始终与我们形影不离休戚与共。光是测量时空的唯一媒体,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基本尺度,是我们建构世界的基本“材料”,是我们确定世界的唯一标准,是我们沟通世界的虔诚信使,也是我们探索宇宙的经典的 Windows。中国人固然缺乏理性的传统,但却并不缺少向往理性的本能直觉。直觉与理性的亲和便是“悟”,悟也即“得道”,得道在我们中国也就是被称之“哲学”的东西。哲学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了解它们是怎样一个东西,怎样一回事,我们对它有了解,它对于我们就有意义。对于一事物或一类事物的完全了解,是很不容易的,但事物的显著性质,譬如“万物生长靠太阳”,是比较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而易于使我们在此方面对某事物或某类事物,得到了解。如是人生显著的性质被我们了解,此即是所谓哲学意义的“觉解”。此觉解也即“得道”,故哲学也即是觉解人生。譬如我是一介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日突然悟到:原来人生只是围着太阳转圈圈——不是太阳围着我转圈圈,而是我围着太阳转圈圈!这就是“觉解”,这就是哲学。这种凭直觉得到的结果与西人凭“道行(科学)”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卡普拉教授说,“(西方)科学实验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如此令人惊讶。”仁者见之仁才谓之仁,智者见之智才谓之智。《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譬如中国人喝茶,西洋人喝咖啡,中西差别不是“饮食而不知其味”,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是谁摧毁了物质的实在性?是谁改变了经典物理学的概念?是相对论?是量子论?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从另一种意义上又不全对。确切地说,是光,是光的波粒二象性,是光的恒定的速度。一部人类科学史,就是一部光学史,光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光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我们生活在光之中,我们睁开眼就和光打交道。光是我们生命之最,有了光就有了一切,我们却不知道感恩给我们带来这一切的“上帝”。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至此,唯光论闪亮登场了。这种新的认识论正是一种来源于直觉然后上升到理性的过程。大概只有像作者本人这样的农夫才能获得这种直觉:人类的生命活动就是接受自然纯粹的太阳光以及挖掘储存了的太阳光,转换它们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换成哲学语言,就是“感光”与“转换光”,就是这么简单,简单的就像用“奥卡姆剃刀”雕琢出来的,但却涵盖了认识论的所有概念。难道承载人类的地球不也是这样吗?否则,怎样解释她不是弃太阳而去,而是虔诚地始终不渝地围绕太阳旋转。太阳光难道不是这个地球以及居住其上的生物的第一需要吗?所以“唯光论”就应该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第一哲学”。唯光论的运动就其在“原子”内部而言,既与古代原子论不谋而合,又与现代光的波粒二象性十分巧合。
如上所述,量子论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意识的参与是波函数坍缩的原因。只有当电子的随机选择结果被人意识到了,它才真正地变为现实,从波函数中脱胎而出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只要它还没有“被意识到”,波函数便总是留在不确定的状态,只不过从一个地方不断地往最后一个测量仪器那里转移罢了——这是被称为“百年罕见天才”的冯·诺伊曼在为量子论做出的杰出数学量化贡献时得出的结论。对于量子论中的观测问题,维格纳的意见是:意识无疑在触动波函数中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维格纳论证说,意识可以作用于外部世界,使波函数坍缩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外部世界的变化可以引起我们意识的改变,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原理,意识也应当能够反过来作用于外部世界。但问题是,“意识”究竟是什么呢?它是独立于所谓“物质”的吗?它服从物理定律吗?它可以存在于低等动物身上吗?它可以存在于机器中吗?很显然,它带来的问题比光的波函数本身要多得多,这些问题是我们沿用“传统的”经典物理观念理解“意识”所产生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哲学唯光论出发,把“意识”理解为 “光子”、波函数或者干脆是“光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是光的参与导致波函数的坍缩及光的“多米诺效应”。所谓“观测行为”是观测者与被观测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就是“感光”与“转换光”。“量子论不容许对自然作完全客观的描述”——海森伯如斯说。意识及其主观的参与是不可避免的。1979 年,在爱因斯坦 100 周年诞辰的纪念会上,爱因斯坦的同事、也是玻尔的密切合作者之一约翰·惠勒提出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构想,也就是所谓的“延迟实验”。在惠勒的构想提出五年后,马里兰大学的卡洛尔·阿雷和其他同事当真做了一个延迟实验,其结果真的证明,我们何时选择光子的“模式”,对于实验结果是没有影响的。这说明,宇宙的历史,可以在它实际发生后才被决定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样一来,宇宙本身由一个有意识的观测者创造出来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宇宙的行为从道理上讲已经演化了几百亿年,但某种“延迟”使得它直到被一个高级生物所观察才成为确定——正像此刻站在历史舞台上的这个家伙、伟大的子宫子因为其发现了“唯光论”而改变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一样。我们的观测行为本身参与了宇宙的创造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参与性宇宙”模型。这实际上是“人择原理”的增强版。
问题又回到两千五百年前,那个中国春秋时期的耄耋老者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几成谶语箴言!自古以来,阐释此言者不下三千余家,历代辈出各出己意,师其成心以自用。唯光论以“执两用中”之“光”释“道”,“道”为“取实予名”之“光”。道恒有名,便是光。名既已出,形随名至。上面提到,“意识”也似“无形”,实则“光”(在无形中)至也,于是,“有生于无”或无中生有,终归不谬也。
根据《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七万年前的认知革命改变了智人的心智,让原本并不占优的非洲猿类成为地球的统治者。智人的心智经过提升后,能够接触到主体间的领域,于是创造了神和企业,建立了城市和帝国,发明了文字和货币,最后也能够分裂原子,登上月球。这种翻天覆地的革命,只是因为智人的 DNA 发生了一点小的变化,大脑神经稍微调整了一下布线。如果真是这样,当代科技人文主义或许只需要对人类的基因再多做些改变,将大脑再稍微调整一下布线,便足以启动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心智改造,让人类能够接触主体间的领域,从而让智人成为地球的统治者;而第二次认知革命,完全可能让智神接触到目前还难以想象的新领域,让智神成为整个星系的主人。然而,即便是作者本人,对这种人工智能必将取代人类意识的伦理趋向,也持怀疑态度:智能与意识,究竟哪一个才更有价值?
从智人到智神,这期间认知革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就是“唯光论事件”。这是与此前任何时期大不相同之处。有关光的认知已经造成智人世界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根据进化论——应该是“天演论”,任何万物灵长所谓的进化,都是基因密码的反应。无论是智人的意识还是智神的智能,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光的“基因密码”,而人类意识与人工智能的理论佯谬,只不过是光的波粒二象性,在科技人文主义或数据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上的幽灵再现而已。唯光论永远是那个引领智人到超智人到智神到超智神的超级天使。
英国著名诗人蒲伯(Alexander Pobe)在为牛顿的墓志铭中写道:“自然和自然规律深藏在黑暗,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于是霞光满天。”200 余年后,又一位英国诗人斯圭尔(J.C.Squire)依样为爱因斯坦写出墓志铭:“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魔鬼咆哮着,嗬!让爱因斯坦来吧!于是,宇宙恢复了漫天霞光。”无独有偶,在千禧年第二个年头,霍金 60 大寿收到一个非常珍贵的纪念品杯子,上面镌刻着霍金那惊为天人的证明黑洞理论的计算公式——这道公式最终定格在霍金与巨人为邻的西敏寺的墓志铭上——“霍金说……于是黑洞发出光来”。三位世界巨人的伟大接力,其接力棒都是“光”。约翰·惠勒有一句名言:It from bit——万物源于比特。子宫子正其本溯其源:It from light——一切皆源自光!
不言而喻,量子力学的世界图景源自“形而尚中”的唯光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唯光论是这个世界的最终主宰?!生活在这个充满无限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世界上,上帝已经赐予我们无限的权利。我们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原来,光就是我们自己,神就是我们自己。这正应验了中国另一位伟大的圣人之谶语箴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哲学唯光论建构的三个纲领…………………………… 001
第二章 唯光论——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说起…………………… 035
第三章 唯光论——从物质的嬗变到哲学观念的嬗变… …… 089
第四章 从原子论到唯光论……………………………………… 108
第五章 哲学唯光论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153
第六章 唯光论——“量子论之后”的哲学… ………………… 179
第七章 “取实予名”的道与实用主义的“光”… ……………… 214
第八章 唯光论与“中立一元论”………………………………… 248
第九章 唯光论与“机体论”……………………………………… 288
第十章 感觉的分析与“感生、转换光”的分析………………… 337
附录一 唯光论释道… …………………………………………… 396
附录二 论儒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哲学思想……………………… 412
附录三 唯光论是一种人本主义 [1]……………………………… 442

